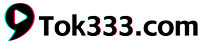责任编辑: vizyon21y.com
拉斐尔•纳达尔还是宣布退役了。他已经好久没有规律地打过比赛了,他陷入了受伤、养伤、短暂地复出而又受伤的循环。当一位职业球员到了他的年纪,再遭遇这样反复的伤病,人们就会意识到他的职业生涯已进入倒计时了。
但是纳达尔却是例外,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像蛮牛一样的纳达尔,他还可能会怎样地虐待自己的身体。因为他仿佛只要还能奔跑,就会试着重新拿起球拍。
纳达尔的理疗师在他25岁时为他检查膝盖,后来他向媒体透露:这是一个35岁的人的膝盖。纳达尔的身体机能其实早已老化得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
这是纳达尔打球的方式决定的——他总是习惯站在底线的深处接发球,当对手势大力沉的发球来到这个位置时,球速会减弱一些,这样再去击球会更精准;但是这样做的坏处也很明显,他要付出更大的击球力量,和比别人更多的跑动。如果对手攻击对角线,他需要更多的横向跑动来弥补弧长;如果对手放小球调动,那么他需要快速移动到前场;对纳达尔来说,他的半场比别人更大,这意味着他需要用脚步填补这些多出来的距离。
于是你会看到纳达尔像一只野兔一样在球场上疾驰。这变成了渐渐他的一种风格与美学,在这种快速跑动的基础之上,他演化出了独属于他自己的标识——他无与伦比的滑步,以及伴随着滑步的标志性正手挥拍,你会看到他的小臂在击球之后,由于身体惯性在脑后盘旋一周,犹如一种表演性的游戏招式。
而跑动只是其中的一步,他还要知道如何停下来,如何控制他的身体在某个支撑点发力,这需要运用他的膝盖,他那伤痕累累不堪重负的膝盖。当他的凌波微步急刹在某一个合适的位置,他就会祭出那炫目的、教科书般的正拍随挥。
这是如同七伤拳般的打法,他的滑步与他的急停,让他拥有优势也在戕害他的身体。于是你会明白,为什么他的每一次击球都是一次自我透支。还好有红土,红土赛场的滑动摩擦力是最小的,将纳达尔的跑动和步伐放在红土赛场,如同鱼入大海。
这就是“红土之王”的由来。拉斐尔•纳达尔拿到了14次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他是罗兰加洛斯球场的宠儿。在刚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最后进入主会场的几位火炬手中,其中一位就是纳达尔,他是唯一的一位外籍运动员,其余选手都来自东道主法国。我有一瞬间还觉诧异,但很快就理解到:纳达尔早已经征服了法国,这是属于他的授勋仪式。
几乎没有人能在罗兰加洛斯球场击败拉斐尔•纳达尔。他在这里享受着无上尊荣,每一次出场山呼海啸的气势,你会以为这里是马德里。巴黎人看着他一次次捧起大满贯奖杯,好像看不腻似的,在许多竞技体育中,一个屡屡胜利的赢家是会遭观众们妒恨的。但他们对纳达尔何其宠溺,法国人却又明明是最厌倦一成不变的。
法网红土的鲜艳颜色一如纳达尔自身的气质,他不像老对手罗杰•费德勒那样白衣飘飘仙风道骨,而是睚眦必报的魔鬼筋肉人。费德勒打球有一种运筹帷幄的气定神闲,而纳达尔满场飞奔的样子惹人哀怜;在与德约科维奇的底线相持中,纳达尔也总是不占优势,德约的球风硬朗,落点深且势大力沉,纳达尔总是用脚步弥补被动场面,他经常应付得相当狼狈。
纳达尔永远不会放弃救球,有时候,对手的回球拉开了一个很大的角度,几乎形成致胜分,他总是快马加鞭赶到。如果幸运的话,你会看到纳达尔的魅力时刻——将极限的救球转化成一次艰难但姿态舒展的反杀。
这是我热爱纳达尔的理由,他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如同武侠小说中,主角被强大的敌人无懈可击的剑阵逼入绝境之时寻找到的一线破绽。
人们热爱纳达尔与费德勒,或许是迷恋那种有如史诗的瑜亮情节。如果他们在历史中交错开,或许都要各添上十座大满贯,但命运注定他们交锋,互相较劲也彼此成就。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天然地不喜欢德约科维奇,他仿佛是插足费纳这台戏的第三者,尽管他甚至在冠军头衔和世界第一的时间上超越了费纳,但却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尴尬的公众印象。
我们仍需对德约科维奇致以莫大的尊重,我犹记得,2012年春天在墨尔本的那场澳网决赛,也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网球比赛,德约科维奇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鏖战击败了纳达尔。二人累到破例被允许坐在小板凳上完成了整个颁奖仪式。在我的回忆里,那场从傍晚开场的比赛一直进行到深夜,我的母亲为我煮了一碗牛肉粥作为夜宵,如今提起澳网,我总有个并不真切的印象——那是充满了香气、温暖而无边无际的夜晚,宛如永恒,我希望两人一直打到第五盘长盘决胜。
然而对我来说,费、纳相较于德约科维奇的特殊之处更在于,在这二者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曾经没有、之后或许再也不会有的灵光,一种行将消失的古典主义残韵。
如何解释这种灵光?它大概意味着,他们都不是后来大行其道的那种“工业流水线球员”(不限于网球)。那种像在游戏设置中将身高、力量、臂展都调到95分的挑不出毛病的六边形战士,他们是什么都有的一代人,除了个性。而他们在身体禀赋上有多完美,他们在赛场的击球选择就有多平庸,因为他们总是在做风险最小的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少搏杀,但却有着一看就被发球机校正过的扎实底线技术,这样或许会减少非受迫性失误,但也难见令人叫绝的致胜分。
而不完美往往意味着,一个球员临渊而立的不安感,那种将命运系在每一次回击的豪赌。就像阿喀琉斯如此强大,但他却有一个脆弱的脚后跟。纳达尔和费德勒走上球场像是在完成某种礼仪。网球只是他们的一件装置,他们好像在用这件事演绎一些别的什么,网球被他们赋予了一种神秘的精神性。在未来的男子网坛,会有层出不穷的辛纳、西蒙、蒂姆、兹维列夫,会有十年一遇的安迪•穆雷和瓦林卡,会有百年一遇的德约科维奇,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纳达尔,也只有一个费德勒。
罗杰•费德勒将热烈与冷静交织于一身。大约在他拿下第五个大满贯之后,他忽然拥有了一种宠辱不惊的本事,之后表现在比赛中的每一秒,像是一种习性。我很喜欢他标志性单手反拍击球时总是带着某种微妙的、自鸣得意的表情,极其淡泊而又睥睨一切。他把网球打得很简单,没有多拍的拉锯较量,而是迅捷一击,落点刁钻。如同《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的智慧与高贵、镇定和从容,费德勒倾倒世人之处在于其风度与冷静,他拥有一种内敛的力量与深不可测的控制力。
而拉斐尔•纳达尔则更像是阿喀琉斯,希腊联军中最强大的战士,也是赫克托尔的宿命敌手,这个人物意味着原始的力量、激情、血气和不屈的韧性。他有他的薄弱关节,就像纳达尔有相当严重的强迫症,他入场时必须先迈右脚,他会准备两瓶水,一瓶冰水一瓶常温,喝水的时候每瓶各喝一口;以及他那繁琐的发球程序——他总要调整肩膀、捋捋长发、刮刮鼻子、扯扯内裤……就好像他与冥冥中的上天曾经做过什么誓约。
这一切都诠释了何谓“风格即人”,他们打球的方式,就是他们灵魂的一面镜子。他们甚至还无比贴切地代表了他们所在国度的气质与风格,费德勒就像他的祖国瑞士,劳力士手表般的尊贵、阿尔卑斯雪山般的优雅和那里广袤牧场的沉静;而纳达尔也像他的西班牙,既有斗牛士的激亢,也有蛮牛般的嗜血,他奔跑起来的高蹈热烈又多么像弗拉门戈的舞步。
如果说费德勒为网球运动带来的是一种贵族般的优雅,那么纳达尔则为这项运动注入了一种史诗般的悲剧性——他与宿敌斗争、与自己的身体斗争、也与命运斗争。他的生涯晚期反反复复的伤病一度让人们认为属于他的时代已经提前结束了,2015赛季时,他的战绩曾一落千丈,全年最好的成绩仅仅是法网的八强,2016年的手腕伤势更是雪上加霜,那时所有人都以为,他的大满贯数量会定格在14座,然而一年以后的2017赛季,他就夺得了法网与美网两座大满贯,并且让世界排名重返第一,而同样强势归来的罗杰•费德勒则分走了那一年的澳网和温网两座冠军。
纳达尔惺惺相惜的老对手费德勒在2022年正式退役,也是这一年,他年仅19岁的西班牙晚辈卡洛斯•阿尔卡拉斯斩获了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在青年世代里,阿尔卡拉斯是我最为钟爱、最具有个人风格的一位球员,但他的比赛风格反倒更像费德勒而非纳达尔:那种犀利的、潇洒的、不顾一切的进攻。
但我也知道他在我心中永远无法企及费德勒与纳达尔,人们总是会为自己青春时期喜爱的偶像抹上一层不一样的滤镜,怀念具体的人和物,就是在怀念一段已经远去的时间。费、纳所引领的网球“古典时代”,也像那个刚刚过去的时代的缩影,那个温情与敬意的时代,容忍与自由的时代,人们彼此竞争也相互欣赏,人们舍得自己的时间去欣赏一项技艺,也像是在陶冶一种美学。
我想,所谓人类文明,不过是群星闪耀的几个瞬间;很多人的名字和样子你已经遗忘了,但却有一些琐碎的时刻你会永远记得。就像我已经忘了某一场比赛的胜负输赢,但我会记得纳达尔总是脏兮兮的、沾满了汗水与红土的球裤,我也记得费德勒在接发时转动球拍的习惯性动作。许多年之后,当人们试图拼合旧世界的碎片,试图去理解曾经和平体面的生活的样子,就像老欧洲的精神遗民翻阅茨威格的著作那样。我大概会给你寄上一盒费德勒与纳达尔比赛的录影带——这或许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美好的东西之一。
文章编辑: vizyon21y.com